•“深化张謇研究专题学术沙龙”发言选登 •
关于“南通应该成为真正的张謇研究中心”
和“张謇学”的几点思考
(2025年4月24日)
蒋建民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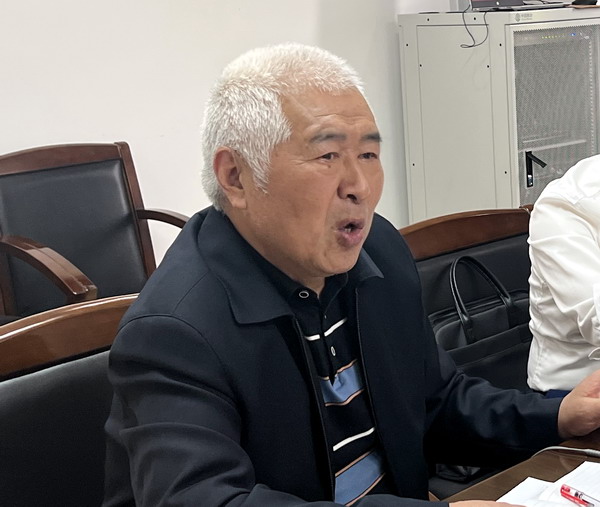
最近,认真地拜读了张廷栖老师关于初探和再探章开沅先生论“张謇学”的两篇文章,可见这位九旬老先生花了不少的心血和功夫。令人非常感动亦十分敬佩!感动和敬佩之余,我也在考虑该怎样发言。讲什么呢?想从章开沅先生的几次讲话入手。
一、关于“南通应该成为真正的张謇研究中心”
章开沅先生在2005年为《张謇研究年刊》写的《我的祝愿(代发刊词)中说,“我始终认为,南通应该成为真正的张謇研究中心,此乃张謇研究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。因为外地(包括海外)优秀的的张謇研究者虽然不乏其人,但大多是个人行动,缺乏必要的当地群体依托……,南通得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之便,理应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张謇研究的真正中心。这里不存在谦虚的问题,更重要的是自觉地承担历史重任的强烈的使命感。”先生的此段讲话,距今已经20年了。先生当年所说的南通“应该成为和理应成为”真正的张謇研究中心,是对南通期望与嘱托,但那时南通尚未形成“真正的张謇研究中心”(什么是“真正的张謇研究中心”?名副其实、众望所归是也)。现如今,20年过去了,先生的期望与嘱托实现了吗?答案是肯定的。20年来,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,南通作为张謇研究的中心地位已经初步凸显;先生对南通建成真正的张謇研究中心的期望与嘱托,也已经初步实现。其标志表现为以下5个方面:1.研究张謇的专门机构和团体越来越多;2.张謇研究的队伍越来越壮大;3.研究张謇的理论成果越来越丰硕(以张謇全集为代表);4.以张謇为主题的学术活动越来越活跃;5.张謇研究的资料文献的整理越来越完善。(时间关系,不一一展开了)
另外我也注意到,除了章开沅先生,关于南通应该成为真正的张謇研究中心的说法。学术界也有类似的观点。南京大学李玉教授2018年在《中国知网张謇主题论文量化分析初阶》一文中认为(以下简称“李文”),“无论机构发文数量,还是个人发文数量,作为张謇家乡的南通都是当之无愧的‘排头兵’,无论政治、经济、实业,还是文化、教育与社会领域的张謇主题文章,发文机构均以南通大学为最多,次则南通纺织技术学院。南通博物苑、张謇研究中心等南通当地文教机构也表现抢眼。……充分说明,南通完全担当了张謇研究的主战场和中心地角色。”(详见《张謇研究年刊2018年》)换一种表述,南通完全担当了张謇研究中心的角色。
因此,把南通建成真正的张謇研究中心的光荣任务,已经历史地落在了我们身上。义不容辞、责无旁贷。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说:“这里不存在谦虚的问题,更重要的是自觉地承担历史重任的强烈的使命感。”简言之,要有舍我其谁的精神。与此同时,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“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仍需努力”。前文中我用了两个“初步”:南通作为张謇研究的中心地位已经初步凸显;先生对南通建成真正的张謇研究中心的期望与嘱托,也已经初步实现。既肯定了南通张謇研究的中心地位(中心角色),也标明了它的状态是初步的或曰初级阶段。真正建成名副其实、众望所归的张謇研究中心,还有许多工作可做。总的来讲,就是前面所说的5个方面的工作(即研究机构、人才队伍、研究成果、学术活动和文献资料)均须进一步优化和提升。尤其是张謇研究的队伍要进一步壮大、张謇研究成果的水平要进一步提高。
先讲研究队伍的壮大。在张謇研究的学术活动中,可见不少精神尚可的银发学者依然活跃在众多的场合。这固然是好事,老同志宝刀未老,贡献智慧。辩证地看,也未必是好事。研究队伍老同志过于壮大,而中青年的比例偏低,不利于事业的可持续发展。比如,《张謇与中国早期现代化——纪念张謇诞辰1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中收入论文49篇,60岁以上的有24篇,接近一半。又如,在今年1月9号召开的纪念张謇研究中心成立40周年座谈会共有10位学者发言,其中有9个在60岁以上,只有1位中青年。再讲一下研究水平的提高。前文我们已经引用了南京大学李玉教授《中国知网张謇主题论文量化分析初阶》的文章。他认为,“无论机构发文数量,还是个人发文数量,作为张謇家乡的南通都是当之无愧的‘排头兵’。”确实如此,从张謇研究成果的数量上分析,说南通的张謇研究占据全国的半壁江山也不为过(文中资料显示南通发文数量综合占比57.8%)。还是李玉的这篇文章,他在“学术反响”的分析中列出了“下载次数”和“被引次数”两个指标,其中,南通人综合占比只有7.6%。这个数据与前面的发文数量形成了较大的反差。学术反响和发文数量的反差较大,说明我们的研究水平有待于提高。事实上,这些年,我们南通作者写的文章虽然很多;但发在权威的学术期刊、史学网站,产生重大影响的成果却很少。
二、关于“张謇学”
本人关于“张謇学”的认识,有个变化。
一是以前曾赞同此说法,并且写过文章。(2017年第1期《江海纵横》上刊出,2018年又以1800字的缩写稿在南通日报发表。现在打开百度搜索“张謇学”,可见拙文《翩然而至的“张謇学”》)
二是近两年不太关注这个说法,主要是受章开沅先生的影响。2013年先生已是87岁高龄了,最后一次来南通,在博物苑参加在纪念张謇16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,“我谈不了多少真正做学问的话,我就是讲一些怎么样把张謇研究,能够在比较长的时间里面延续下去,能够不断地繁荣发展。现在,老争这个是不是‘张謇学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张謇研究的意义是有目共睹、世界公认的。现在的问题是:怎么样把张謇的研究,不断地完善、不断地延续,好的学者一代一代地青胜于蓝,这才是最重要的。”(张謇研究中心编《张謇复兴中华的认识与实践——纪念张謇16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,苏州大学出版社,2014年,第8-9页)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顾问看来,“不断地完善、不断地延续”张謇研究,才是最重要的,而争论“张謇学”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此话怎讲?我的理解,一是,不管怎样争论,作为一门学问的研究,从30多年之前第一次有人提出“张謇学”的概念,它便客观存在了。不管你是否承认;或者说,不管你认为它处于何种阶段(初现端倪、尚在生长、日趋成熟和成熟),从理论上讲,“张謇学”已是客观存在。二是,名称不重要,重要的是把张謇研究做深、做实、做长、做远,亦即章开沅先生所说的“不断地完善、不断地延续”。三是,先生对“张謇学”的认识,也是有变化的。从先前多次论述“张謇学”的必要性和可能性,到晚年不再纠结于“张謇学”的争论,认为没有任何意义。四是,不争论“张謇学”并不意味着不要“张謇学”,而是不急于求成,顺其自然,自有瓜熟蒂落、水到渠成时。
据张廷栖教授《初探章开沅先生论张謇学》(见《江海纵横》2024.3)所述,2016年张謇研究中心的同志去武汉拜访章开沅在谈到“张謇学”时,先生说,“现在来讲‘张謇学’应该是可以了”,“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,你们说‘张謇学’也没什么关系”,“叫张謇学也未尝不可”。问题来了。2013年先生还说“老争这个是不是‘张謇学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”,时隔3年,先生又说“叫张謇学也未尝不可”。这3年, 张謇研究领域发生什么重大变化了吗?是出了 “一批真正可以传世的学术佳作”还是“一批处于国内外先进行列的张謇研究学者”?都没有。那先生为什么“松口了”?不像以前那样“保守”和谨慎了?我觉得可以从三方面去理解。第一,讲此话时,先生已是90高龄,不像以前那么较真了,小范围的非正规场所的讲话,不必过于拘谨,随意些无所谓;第二,即便是如此,请注意先生的语气,比较缓和委婉,并不是十分的肯定。更何况,30年来,“张謇学”一直有人在提,似乎很少有人公开反对过。
引用了张廷栖教授文章的一段文字并附加了自己的理解之后,说说我现在对“张謇学”的看法:1.“张謇学”客观存在;2. (前文中,我曾提出“张謇学”的四个阶段:1.初现端倪;2.尚在生长;3.日趋成熟;4.成熟。)如果说,二三十年之前,“张謇学”初现端倪;一二十年之前,“张謇学”尚在生长;现阶段,保守一点讲,“张謇学”正处于“尚在生长”向“日趋成熟”过渡之阶段,乐观地讲,已处于是日趋成熟之阶段。不管如何,我相信,章开沅先生2006年在南通举办的第四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预言:“只要我们一代又一代不懈努力,成熟的‘张謇学’必将现身于21世纪!”一定会实现。
三、我们怎么办?
1.指导思想上,坚持“四个不断”,即“不断地完善、不断地延续”张謇研究,不断地拓展张謇研究的广度和深度,不断地提升张謇研究队伍的整体水平,为迈向成熟的张謇学打牢基础(前两个“不断”是引用章开沅先生的话)。
2.具体做法上,有四点建议:
第一,鼓励优秀成果,设立创新成果奖。成熟的张謇学,首当其冲的是,涌现出一批高质量的创新性研究成果。放眼望去,现在每年的写张謇的专题文章不少。但实事求是地讲,大多是人云亦云、空洞无物,或是生搬硬套、东拼西凑、新瓶装旧酒。而高质量的、有创新的成果呢?寥寥无几。为鼓励原创,建议设立“张謇研究创新成果奖”。
第二,加强队伍建设,设立优秀人才奖。面向50岁(不含)以下中青年张謇研究爱好者。此举乃是“不断地延续”张謇研究之重要举措。
第三,理论阵地建设。
(1)张謇研究年刊,从今年起,新辟并固定一个栏目:《张謇学》;
(2)张謇研究中心网站,也可以新辟专题:《张謇学》
(3)南通大学张謇研究院定期出版的《张謇与近代中国》,也可以约稿并设置《张謇学》栏目。
(4)海门区张謇研究会主办的内刊《张謇研究》,也可以新辟《张謇学》专栏。
第四,适时制造氛围。明年即2026年8月24日是张謇先生去世100周年,可借机搞一个以构建与培育“张謇学”为主题的学术纪念活动,扩大“张謇学”的宣传和提高“张謇学”的认同度。面向全国征文或约稿,会后将研讨会论文结集出版(最好能公开出版)。
(作者简介:蒋建民,南通市社科联原秘书长)